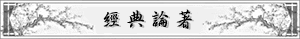|
|
〔疏〕吴曹侍读元忠云:“汉书艺文志:‘扬雄所序三十八篇。'本注云: ‘法言十三。'此十三篇,即本传之十三卷。文选班孟坚答宾戏注引作‘十二卷' 者,宋祁校本云:‘李轨注法言本,渊骞与重黎共序。'知轨据汉世传本,重黎、 渊骞幷为一篇,故合法言序为十三篇,可由祁校语得之。”荣按:李本自学行卷第 一,至孝至卷第十三,每卷标题下皆有注语,惟渊骞卷第十一下无文,盖重黎、渊 骞本为一篇,多论春秋以后国君、将相、卿士、名臣之事,以其文独繁,倍于他篇, 故自篇中“或问渊、骞之徒恶乎在”以下,析为卷第十一。虽自为一篇,然实即重 黎之下半,既非别有作意,遂不为之序。弘范知其然,故于此卷标题下亦不为之注。 艺文志“法言十三”,此据卷数言之则然,若论其作意,不数渊骞,则止十二。答 宾戏注引扬雄传:“譔十二卷,象论语,号曰法言。”此可证旧本汉书此传承用子 云自序,其文如此。卷末所载法言序中之不得别有渊骞序,更不辩自明。浅人习见 通行法言卷数皆为十三,疑雄传“十二卷”字为“十三”之误,又疑渊骞独无序为 传写阙失,遂改“二”为“三”。且妄造“仲尼之后,迄于汉道”云云二十八字, 为渊骞序,窜入传中。于是雄传此文不独非子云之真,亦并非孟坚之旧矣。君直据 选注此条,证明重黎、渊骞共序之义,至为精核。然谓轨据汉世传本合法言序为十 三篇,似亦未协。李本法言序附孝至之后,明不以为一篇。盖重黎、渊骞之析为二 篇,汉世已然。谓法言序无渊骞序,则是;谓十三卷为数序,不数渊骞,则非也。 或问:“渊、骞之徒恶乎在?”曰:“寝。”或曰:“渊、骞曷不寝?”曰: “攀龙鳞,附凤翼,巽以扬之,勃勃乎其不可及也。如其寝!如其寝!”〔疏〕 “渊、骞之徒恶乎在”者,学行注云:“徒犹弟子也。”渊、骞之徒,犹云七十子 之弟子。仲尼弟子列传以颜渊、闵子骞居首,故举渊、骞以统其余也。音义:“恶 乎,音乌。”按:七十子皆身通六艺,而其弟子多不传,故以为问。“寝”者,广 雅释诂:“寝,藏也。”按:谓湮没不彰也。音义:“曰寝,俗本作‘曰在寝', ‘在',衍字。”司马云:“宋、吴本作‘在寝'。”按:此因未解寝字之义而妄 增者。“攀龙鳞,附凤翼”者,伯夷列传云:“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” 索隐云:“喻因孔子而名彰。”即此文所本。巽以扬之,集注本无“巽”字,云: “宋、吴本作‘巽以扬之',今从李本。”是温公所见监本无此字。今治平本有之, 而“巽以扬之”四字占三格,明是修板挤入。秦校云:“当衍‘巽'字,温公集注 可证。”是也。俞云:“卢氏文弨云:‘李本巽作翼。'不知翼者即涉上句‘附凤 翼'而误衍。温公但云‘扬,发扬也',不及翼字之义。是其所据本无‘巽'字, 亦非别有他字也。今各本皆作‘巽以扬之',盖据宋、吴本加,非李本之旧。”荣 按:旧监本固无“巽”字,然此或传写偶脱,非必李本如此。后汉书光武帝纪章怀 太子注引此文正作“巽以扬之”,(各本皆同。)则其所据本有“巽”字,为宋、 吴本所自出,钱本亦有之,于义为足。盖下文勃勃乎其不可及也,即承巽字而言。 巽为风,故云勃勃。龙麟、凤翼喻孔子之道,巽风喻天。言七十子得孔子而师事之, 天实助之,以成其名也。勃勃乎其不可及也,世德堂本作“不可及乎”。“如其寝! 如其寝”者,七十子之成名皆以孔子,七十子之弟子源远而流益分,不复能有所附 丽以成其名,然则七十子之遭际,岂得与其弟子之遭际相提并论也! 七十子之于仲尼也,日闻所不闻,见所不见,文章亦不足为矣。〔疏〕“七十 子之于仲尼也”,司马云:“宋、吴本作‘七十二子'。”按:孟子云:“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。”本书学行云:“速哉!七十子之肖仲尼也。”皆举成数言之,此 亦同。宋、吴本非。“日闻所不闻,见所不见”者,圣人之言行,如天道之日新, 学者得圣人而师之,其进益无有已时也。“文章亦不足为矣”者,司马云:“言游 孔门者,务学道德,不事文章。”按:谓七十子不必皆有著述传于后世,非其才有 所不逮,乃日有所不给,亦意有所不屑也。 君子绝德,小人绝力。或问“绝德”。曰:“舜以孝,禹以功,皋陶以谟,非 绝德邪?”〔注〕是皆德之殊绝。“力”。〔注〕绝力者何?“秦悼武、乌获、任 鄙扛鼎抃牛,非绝力邪?”〔注〕此等皆以多力举重,崩中而死,所谓不得其死然。 〔疏〕“君子绝德,小人绝力”者,绝谓不可几及。言君子小人各有其不可几及者, 君子之于德,小人之于力是也。“舜以孝”者,尧典云:“有鳏在下,曰虞舜,父 顽,母嚚,象傲,克谐以孝。”中庸云:“舜其大孝也与?德为圣人,尊为天子, 富有四海之内,宗庙飨之,子孙保之。”“禹以功”者,禹贡云:“禹锡玄圭,告 厥成功。”左传昭公篇云:“美哉禹功!明德远矣。微禹,吾其鱼乎?”“皋陶以 谟”者,皋陶谟云:“曰若稽古皋陶曰:‘允迪厥德,谟明弼谐。'”书序云: “皋陶矢厥谟。”“秦悼武、乌获、任鄙扛鼎抃牛”者,秦本纪云:“惠王卒,子 武王立。”索隐云:“名荡。”按:本纪称武王者,省言之。下云“悼武王后出归 魏”,又始皇本纪云“悼武王享国四年,葬永陵”,是以二字为谥也。本纪又云: “武王有力好戏,力士任鄙、乌获、孟说皆至大官。王与孟说举鼎绝膑,八月, (按:悼武四年。)武王死,族孟说。”是乌获、任鄙皆秦悼武王同时人。孟子云: “然则举乌获之任,是亦为乌获而已矣。”赵注云:“乌获,古之有力人也。”则 乌获乃古有力者之称。秦悼武王时之乌获,以有力着,因取此名名之耳。梁氏玉绳 汉书人表考云:“案文子自然篇,老子曰:‘用众人之力者,乌获不足恃。'是古 有乌获,后人慕之,以为号也。”樗里子甘茂列传云:“秦人谚曰:‘力则任鄙, 智则樗里。'”音义:“扛鼎,音江。”司马云:“抃牛,谓以两牛相击,如抃手 状。”按:张平子思玄赋旧注云:“抃,手搏也。”又通作“卞”,汉书哀帝纪赞 苏林注云“手搏为卞”,是也。然则抃牛即手搏牛之谓。殷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: “纣倒曳九牛。”注“是皆德之殊绝”。按:司马长卿封禅文:“未有殊尤绝迹可 考于今者也。”是殊、绝义同。注“此等皆以多力举重,崩中而死”。按:世德堂 本无“此等”二字。秦本纪:“举鼎绝膑。”集解引徐广云:“一作‘脉'。”弘 范所据史记,字盖作“脉”,故云崩中。内经阴阳别论云:“阴虚阳搏谓之崩。” 王注云:“阴脉不足,阳脉盛搏,则内崩而血流下。”即其义。史记惟言秦武王举 鼎而死,今按告子孙疏引皇甫士安帝王世说(当作“世纪”。)云:“秦武王好多 力之士,乌获之徒并皆归焉。秦王于洛阳举周鼎,乌获两目血出。”则乌获盖亦不 得其死。任鄙死状未闻。白起列传云:“昭王十三年,穰侯相秦,举任鄙以为汉中 守。”则鄙至昭襄王时犹存。弘范云此等皆以举重死,或别有所本。 或问“勇”。曰:“轲也。”曰:“何轲也?”曰:“轲也者,谓孟轲也。若 荆轲,君子盗诸。”请问“孟轲之勇”。曰:“勇于义而果于德,不以贫富、贵贱、 死生动其心,于勇也,其庶乎!”〔注〕或人之问勇,犹卫灵公之问陈也。仲尼答 以俎豆,子云应之以德义。〔疏〕“若荆轲,君子盗诸”者,刺客列传云:“荆轲 者,卫人也。其先乃齐人,徙于卫,卫人谓之庆卿。而之燕,燕人谓之荆卿。”索 隐云:“轲先齐人,齐有庆氏,则或本姓庆。春秋庆封,其后改姓贺,此亦至卫而 改姓庆尔。荆、庆声相近,故随在国而异其号也。”又同传正义引燕太子篇云: “荆轲神勇之人,怒而色不变。”吴云:“为燕太子刺秦王,以君子之道类之,则 大盗耳。”司马云:“比诸盗贼。”按:义详后文。“请问孟轲之勇”,治平本无 “问”字,钱本同,今依世德堂本。“勇于义而果于德,不以贫富、贵贱、死生动 其心”者,吴云:“养浩然之气,勇之大者。”按:“孟子云:‘我四十不动心。' 曰:‘若是,则夫子过孟贲远矣。'”赵注云:“孟子勇于德。”又:“孟子云: ‘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 为气也,配义与道,无是馁也。'”又云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 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“其于勇也,其庶乎”者,荀子性恶云:“天下有中,敢直 其身;先王有道,敢行其义。上不循于乱世之君,下不俗于乱世之民。仁之所在亡 贫穷(一),仁之所亡无富贵。天下知之,则欲与天下共苦乐之;天下不知之,则 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。是上勇也。”注“或人”至“德义”。按:世德堂本 “犹”作“若”;“应之以德义”,无“之”字。(一)“亡”字原本讹作“虽”, 据荀子性恶篇改。 鲁仲连●而不制,〔注〕高谈以救时难,功成而不受禄赏。蔺相如制而不●。 〔注〕好义崇理,屈身伸节,辅佐本国,系时之务也。〔疏〕“鲁仲连●而不制” 者,鲁仲连邹阳列传云:“鲁仲连者,齐人也,好奇伟俶傥之画策,而不肯仕官任 职,好持高节。游于赵,会秦围赵,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,乃见平原君曰:‘事 将柰何?'平原君曰:‘胜也何敢言事?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,今又内围邯郸而不 能去。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,今其人在是,胜也何敢言事?'鲁仲连曰: ‘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,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。梁客新垣衍安 在?吾请为君责而归之。'鲁仲连见新垣衍曰:‘昔者齐愍王欲行天子之礼于邹、 鲁,邹、鲁之臣不果纳。今秦万乘之国也,梁亦万乘之国也,俱据万乘之国,各有 称王之名,睹其一战而胜,欲从而帝之,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、鲁之仆妾也。且 秦无已而帝,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。彼将夺其所不肖,而与其所贤;夺其所憎,而 与其所爱。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,处梁之宫,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?而 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?'于是新垣衍起,再拜谢,不敢复言帝秦。适会魏公子无忌 夺晋鄙军以救赵,击秦军,秦军遂引而去。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,鲁连辞让。使者 三,终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,酒酣起,前以千金为鲁连寿。鲁连笑曰:‘所为贵 于天下之士者,为人排患释难,解纷乱而无取也。即有取者,是商贾之事也,而连 不忍为也。'遂辞平原君而去,终身不复见。其后二十余年,燕将攻下聊城,聊城 人或谗之燕,燕将惧诛,因保守聊城不敢归。齐田单攻聊城,岁余,士卒多死,而 聊城不下。鲁连乃为书,约之矢,以射城中,遗燕将。燕将见鲁连书,犹预不能自 决。欲归燕,已有隙,恐诛;欲降齐,所杀虏于齐甚众,恐已降而后见辱,乃自杀。 聊城乱,田单遂屠聊城,归而言鲁连,欲爵之。鲁连逃隐于海上,曰:‘吾与富贵 而诎于人,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。'”音义:“●与荡同。”司马云:“宋、吴本 ‘●'作‘●',‘制'作‘剬'。介甫曰:‘●古荡字,剬古制字。'”按:说 文:“愓,放也。”古书多假“荡”为之。●、●皆“愓”之俗。玉篇:“●,他 莽切,直也。”非此文之义。五帝本纪:“依鬼神以剬义。”正义云:“剬古制字。” 梁氏志疑云:“古制字作‘制',若‘剬',音端,与‘剸'同。则‘剬'乃‘制' 之讹矣。”按:篆文制作“●”,隶变作“●,传写遂误为“剬”耳。●谓自适, 制谓自持。鲁仲连●而不制,谓其能轻世肆志,而不能仕官任职。蔺相如,见重黎 疏。制而不●,谓其能惩忿以先国家之急,而尝为宦者令缪贤舍人,亦降志辱身矣。 司马云:“仲连不以富贵动其心,而未能忘死生;相如不以死生动其心,而未能忘 富贵,故云然。”温公意以此为承上章而言,故释之如此,然义似未确。注“功成 而不受禄赏”。按:世德堂本作“爵赏”。注“好义崇理”。按:世德堂本作“崇 礼”。 或问“邹阳”。曰:“未信而分疑,慷辞免罿,几矣哉!”〔注〕鸟罟谓之罿, 犹人之缧绁。几,危也。狱中出慷慨之词,得以自免,亦已危矣。〔疏〕史记邹阳 与鲁仲连同传,既论鲁仲连,故遂及邹阳也。彼传云:“邹阳者,齐人也,游于梁, 与故吴人庄忌夫子、淮阴枚生之徒交,上书,而介于羊胜、公孙诡之间。胜等忌邹 阳,恶之梁孝王。孝王怒,下之吏,将欲杀之。邹阳客游,以谗见禽,恐死而负累, 乃从狱中上书。书奏梁孝王,孝王使人出之,卒为上客。”太史公曰:“邹阳辞虽 不逊,然其比物连类,有足悲者,亦可谓抗直不挠矣。”“未信而分疑”者,宋云: “言未为梁王所信,方为其所疑,虽能分解以免,固亦危矣。”司马云:“孔子称 信而后谏,未信则以为谤己也。阳初仕梁,未为孝王所信,而深言以触机事,分取 孝王之疑,故曰未信而分疑。”吴胡部郎玉缙云:“疑,谤也。未信而分疑,未信 而致与人分谤也。邹阳云:‘为世所疑。'谓为世所谤,杨子盖本此。”荣按:邹 阳书云:“臣闻忠无不报,信不见疑,臣常以为然,徒虚语耳。昔者荆轲慕燕丹之 义,白虹贯日,太子畏之。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,太白蚀昴,而昭王疑之。夫精 变天地,而信不喻两主,岂不哀哉!今臣尽忠竭诚,毕议愿知。左右不明,卒从吏 讯,为世所疑。是使荆轲、卫先生复起,而燕、秦不悟也。愿大王孰察之!'”是 书意以疑、信对举,疑即不信之谓。曲礼:“分争辩讼。”郑注云:“分、辩皆别 也。”然则分疑即辩疑,似以宋义为长。“慷辞免罿”者,音义:“慷辞,苦两切。 免罿,音冲。”按:说文:“抗,扞也。”引伸为不诎之义。慷辞即抗辞,史云邹 阳辞不逊,及云抗直不挠,是也。“几矣哉”者,音义:“几矣,音机。”按:重 黎云:“如辩人,几矣!”与此同义。注“鸟罟谓之罿”。按:说文:“罿,罬也”; “罬,捕鸟覆车也”。尔雅释器:“罬谓之罦。罦,覆车也。”郭云:“今之翻车 也,有两辕,中施罥以捕鸟。”王氏筠说文释例云:“覆车,吾乡谓之翻车,不用 罔目,以双绳贯柔条,张之如弓,绳之中央缚两竹,竹之末箕张亦以绳贯之,而张 之以机。机上系蛾,鸟食蛾则机发,竹覆于弓,而●其项矣。以其弓似半轮,故得 车名。”注“狱中出慷慨之辞”。按:弘范读慷如字,故以为慷慨之辞。慷即“■” 之俗,说文:“慷,慨也。”又“慨”篆下云:“慷慨,壮士不得志也。”然“慷 辞”字明用史公邹阳传赞语,意非慷慨之谓,此注似失其义。 或问:“信陵、平原、孟尝、春申益乎?”曰:“上失其政,奸臣窃国命,何 其益乎!”〔注〕当此四君之时,实皆有益于其国,而杨子讥之者,盖论上失其政, 故辩明之。〔疏〕“信陵、平原、孟尝、春申益乎”者,信陵君列传云:“魏公子 无忌者,魏昭王少子,而魏安厘王异母弟也。昭王薨,安厘王即位,封公子为信陵 君。公子为人仁而下士,士无贤不肖,皆谦而礼交之,不敢以其富贵骄士。士以此 方数千里争往归之,致食客三千人。当是时,诸侯以公子贤,多客,不敢加兵谋魏 十余年。魏有隐士曰侯嬴,年七十,家贫,为大梁夷门监者。公子闻之,从车骑, 虚左,自迎夷门侯生,侯生遂为上客。魏安厘王二十年,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,又 进兵围邯郸。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,数遗魏王及公子书,请救于魏。魏 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。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:‘吾攻赵,旦暮且下,而诸侯 敢救者,已拔赵,必移兵先击之。'魏王恐,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,名为救赵,实 持两端以观望。公子患之,因问侯生。乃屏人间语曰:‘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 内,而如姬最幸,力能窃之。公子诚请如姬,如姬必许诺,则得虎符,夺晋鄙军, 北救赵而西却秦。'公子从其计,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。公子行,侯生曰: ‘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。此人力士,晋鄙听,大善;不听,可使击之。'公子遂行。 至邺,矫魏王令代晋鄙。晋鄙合符,疑之,欲无听。朱亥袖四十斤■椎椎杀晋鄙, 公子遂将晋鄙军,得选兵八万人,进兵击秦军,秦军解去,遂救邯郸,存赵。魏王 怒公子之盗其兵符,矫杀晋鄙。公子亦自知也,使将将其军归魏,而独与客留赵, 十年不归。秦日夜出兵东伐魏,魏王患之,使人往请公子,公子归救魏。魏王以上 将军印授公子,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。秦王患之,乃行金万斤于魏,求晋 鄙客,令毁公子于魏王。魏王日闻其毁,不能不信,后果使人代公子将。公子自知 再以毁废,乃谢病不朝,与宾客为长夜饮。饮醇酒,多近妇女,日夜为乐饮者四岁, 竟病酒而卒。”索隐云:“地理志无信陵,或曰是乡邑名。”又平原君虞卿列传云: “平原君赵胜者,赵之诸公子也。诸子中,胜最贤,喜宾客,宾客盖至者数千人。 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,三去相,三复位,封于东武城。秦之围邯郸,赵使平 原君求救合从于楚。平原君已定从而归,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,魏信陵君亦矫夺 晋鄙军往救赵,皆未至。秦急围邯郸,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令夫人以下编于 士卒之间,分功而作,家之所有,尽散以飨士。平原君从之,得敢死之士三千。李 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,秦军为之却三十里。亦会楚、魏救至,秦兵遂罢,邯郸复存, 李同战死。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,子孙代后,竟与赵俱亡。”又孟尝君列传 云:“孟尝君名文,姓田氏。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。田婴者,齐威王少子,而齐宣 王庶弟也。田婴相齐十一年,宣王卒,泯王即位,封田婴于薛。文承间问其父婴曰: ‘君用事相齐,至今三王矣。齐不加广,而君私家富累万金,门下不见一贤者,文 窃怪之。”于是婴乃礼文,使主家,待宾客,宾客日进,名声闻于诸侯,诸侯皆使 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,婴许之。婴卒,而文果代立于薛,是为孟尝君。孟尝君 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,皆归孟尝君,孟尝君舍业厚遇之,以故倾天下之 士,食客数千人,无贵贱,一与文等。秦昭王闻其贤,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,以 求见孟尝君。齐泯王二十五年,卒使孟尝君入秦,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。人或说 秦昭王曰:‘孟尝君贤,而又齐族也,今相秦,必先齐而后秦,秦其危矣。'秦昭 王乃止,囚孟尝君,谋欲杀之。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。姬曰:‘妾愿得君狐 白裘。'孟尝君有一狐白裘,直千金,天下无双。入秦,献之昭王,更无他裘。客 有能为狗盗者,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,取所献狐白裘至,以献秦王幸姬。幸姬为言 昭王,昭王释孟尝君。孟尝君得出,即驰去。夜半至函谷关,关法鸡鸣而出客,孟 尝君恐追至,客有能为鸡鸣,而鸡尽鸣,遂发传出。出如食顷,秦追果至关,已后 孟尝君出,乃还。齐泯王不自得,以其遣孟尝君。孟尝君至,则以为齐相任政。居 数年,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泯王,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。后齐泯王灭宋,益骄,欲 去孟尝君。孟尝君恐,乃如魏,魏昭王以为相,西合于秦、赵,与燕共伐破齐。齐 泯王亡在莒,遂死焉。齐襄王立,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,无所属。齐襄王新立,畏 孟尝君,与连和复亲(一)。薛公卒,谥为孟尝君。诸子争立,而齐、魏共灭薛, 孟尝绝嗣,无后也。”索隐云:“孟尝袭父封薛,而号曰孟尝君。此云谥,非也。 孟,字;尝,邑名。尝邑在薛之旁。”按:文袭父封,本为薛公,别号孟尝君,死 而遂以为谥,犹父谥靖郭君之比,谥亦号也。又春申君列传云:“春申君者,楚人 也,名歇,姓黄氏。游学博闻,事楚顷襄王,使于秦。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、魏共 伐楚,未行而楚使黄歇适至于秦,闻秦之计。当是之时,秦已前使白起攻楚,取巫、 黔中之郡,拔鄢、郢,东至竟陵。楚顷襄王东徙,治于陈县。黄歇恐一举而灭楚, 乃上书说秦昭王,昭王乃止白起而谢韩、魏,发使赂楚,约为与国。黄歇受约归楚, 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,秦留之数年。楚顷襄王病,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:‘今 楚王恐不起疾,秦不如归其太子,太子得立,其事秦必重,而德相国无穷,是亲与 国而得储万乘也。'应侯以闻秦王,秦王曰:‘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,返 而后图之。'黄歇为太子计,变衣服为楚使者,御以出关,而黄歇守舍,常为谢病。 度太子已远,秦不能追,歇乃自言秦昭王,愿赐死。秦因遣黄歇。歇至楚三月,楚 顷襄王卒,太子完立,是为考烈王。以黄歇为相,封为春申君。是时齐有孟尝君, 赵有平原君,魏有信陵君,方争下士,招致宾客,以相倾夺,辅国持权。春申君为 楚相四年,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;五年,围邯郸,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,秦 兵亦去。春申君相楚八年,北伐灭鲁,以荀卿为兰陵令。春申君相二十二年,诸侯 患秦攻伐无已时,乃相与合从西伐秦,而楚王为从长,春申君用事。至函谷关,秦 出兵攻诸侯兵,皆败走,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,春申君以此益疏。楚于是去陈,徙 寿春。楚考烈王无子,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(二),闻其不宜子,恐久无 宠,求事春申君为舍人,乃进其女弟,即幸于春申君。知其有身,乃与其女弟谋, 承间以说春申君曰:‘君贵,用事久,多失礼于王兄弟,祸且及身。今妾自知有身 矣,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,妾赖天有子男,则是君之子为王也,楚国尽可得, 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?'春申君大然之,乃出李园女弟谨舍,而言之楚王。楚王召 入幸之,遂生子男,立为太子。李园恐春申君语泄,阴养死士,欲杀春申君以灭口。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,楚考烈王卒,李园伏死士于棘门之内,春申君入棘门园,死士 侠刺春申君,斩其头,投之棘门外,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。”正义云:“四 君封邑检皆不获,唯平原有地,又非赵境,并盖号谥,而孟尝是谥。”“上失其政, 奸臣窃国命,何其益乎”者,汉书游侠传云:“古者天子建国,诸侯立家,自卿大 夫以至于庶人,各有等差。是以民服事其上,而下无觊觎。孔子曰:‘天下有道, 政不在大夫。'百官有司,奉法承令,以修所职。失职有诛,侵官有罚。夫然故上 下相顺,而庶事理焉。周室既微,礼乐征伐自诸侯出,桓、文之后,大夫世权,陪 臣执命。陵夷至于战国,合从连衡,力政争强。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,赵有平原, 齐有孟尝,楚有春申,皆借王公之埶,竞为游侠,鸡鸣狗盗,无不宾礼。皆以取重 诸侯,显名天下,搤■而游谈者,以四豪为称首。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,守职奉上 之义废矣。”按:孟坚此论,原本儒术,可为此文之义疏。(一)“亲”下原本有 偏书小字“句”,盖作者以示句读,今删。(二)“王”下原本有偏书小字“句”, 盖作者以示句读,今删。 樗里子之知也,使知国如葬,则吾以疾为蓍龟。〔注〕疾者,樗里子之名。死 葬,豫言后当有两天子宫夹我,果如其言。使其策算国事如之,则吾以疾为蓍龟者, 有为有行动而问焉。〔疏〕“樗里子之知也”,世德堂本“知”作“智”。按:音 义出“之知”,云:“音智,下‘知国'如字。”明不作“智”。樗里子甘茂列传 云:“樗里子者,名疾,秦惠王之弟也。樗里子滑稽多智,秦人号曰智囊。秦惠王 卒,太子武王立,以樗里子、甘茂为左、右丞相。秦武王卒,昭王立,樗里子又益 尊重。昭王七年,樗里子卒,葬于渭南章台之东,曰:‘后百岁,是当有天子之宫 夹我墓。'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,渭南阴乡樗里,故俗谓之樗里子。至汉兴, 长乐宫在其东,未央宫在其西,武库正直其墓。秦人谚曰:‘力则任鄙,智则樗里。'” 索隐云:“樗,木名也,音摅。高诱曰:‘其里有樗树,故曰樗里。'然疾居渭南 阴乡之樗里,故号曰樗里子。又纪年则谓之褚里疾。”“使知国如葬,则吾以疾为 蓍龟”者,世德堂本作“使知国如知葬”。樗里子为秦相,未闻有所益于国,而独 以知葬闻,是其智不足称也。盖谓樗里子知葬云云者,本秦人传言之妄,此不斥其 妄,而惜樗里子之不能用其智于国,明传言即非妄,亦不可以为智也。袁彦伯三国 名臣序赞(一):“思同蓍蔡。”李注引此文作“樗里之智也,使知国若葬,吾以 疾为蓍蔡也”。似旧本“龟”作“蔡”。论语:“臧文仲居蔡。”苞云:“蔡,国 君之守龟也。出蔡地,因以为名焉。”注“疾者”至“问焉”。按:世德堂本此注 全删。“策算”钱本作“算策”。(一)“彦伯”二字原本互倒,据文选改。 “周之顺、赧,以成周而西倾;秦之惠文、昭襄,以西山而东幷,孰愈?”曰: “周也羊,秦也狼。”“然则狼愈与?”曰:“羊、狼一也。”〔注〕过犹不及, 两不与也。〔疏〕“周之顺、赧,以成周而西倾”者,音义:“周之顺、赧,诸本 皆作‘顺、赧',顺靓王及赧王也。俗本作‘周之倾',字之误也。史记作‘慎靓 王',索隐作‘顺靓王',或是‘慎'转为‘顺'。赧,奴板切。”司马云:“宋、 吴本作‘周之倾赧'。”按:周本纪:“显王崩,子慎靓王定立。”梁氏志疑云: “晋常璩华阳国志作‘慎王',而路史前纪注引志作‘静王',又作‘顺王',盖 单称之耳。靓即静字,顺与慎通。”按:逸周书谥法:“慈和遍服曰顺。”别无 “慎”字,明慎即顺也。作“倾”者,顺、倾形近,兼涉下文“西倾”字而误。本 纪又云:“慎靓王立六年崩,子赧王延立。”按:详重黎疏。成周,周敬王至顺靓 王所都之东周也。自春秋至战国,东周凡三:其一,平王以后所都之王城也。诗黍 离序郑笺云:“宗周,镐京也,谓之西周。周,王城也,谓之东周。”是也。其二, 敬王以后所都之成周也。公羊传昭公篇云:“王城者何?西周也。成周者何?东周 也。”是也。其三,考王之弟之孙所封之巩也。周本纪索隐云:“西周,河南也。 东周,巩也。”是也。汉时,王城为河南县,成周为雒阳县,巩为巩县,并属河南 郡。宋云:“平王东迁于洛,即周公所营之王城,是谓成周。”此误以河南县与雒 阳县牵合为一也。周本纪:“王赧徙都西周。”正义云:“敬王从王城东徙成周, 十世至王赧,从成周西徙王城。”然则王赧之时已去成周而复都王城,此云以成周 西倾者,因兼举顺靓王,从其前者言之耳。西倾谓王赧奔秦,(本纪书“西周君”。 正义以为西周武公,误也。)尽献其邑三十六,口三万,是也。“秦之惠文、昭襄 以西山而东幷”者,秦本纪:“孝公卒,子惠文君立。”索隐云:“名驷。”又本 纪:“武王取魏女为后,无子,立异母弟,是为昭襄王。”索隐云:“名则,一名 稷,武王弟。”按:武王即悼武王,为惠文君子,昭襄为悼武弟,亦惠文子也。吴 云:“秦都雍州,西山在焉,而东灭周,故曰东幷。”本纪曰:“文公卒,葬西山。” 按:秦文公葬地,据集解引皇甫谧云,在今陇西之西县,则当今甘肃巩昌府西和县 境。此文西山,不当指此。易随“上六,王用亨于西山”,又升“六四,王用亨于 岐山”,毛氏奇龄仲氏易云:“西山者,岐山也。”焦氏循易章句亦云:“岐山犹 西山也。”然则此即用易文,西山犹云岐山耳。地理志:“右扶风美阳,禹贡岐山 在西北中水乡,周太王所邑。”音义:“东幷,音并。”新书过秦云:“孝公既没, 惠文、武、昭襄蒙故业,因遗策南取汉中,西举巴蜀,东割膏腴之地,北收要害之 郡,诸侯恐惧。”秦本纪云:“昭襄王五十一年,西周君走来自归,顿首受罪。” 按:不云庄襄、始皇者,以周之亡在昭襄之世也。“孰愈”者,问道云:“或问: ‘狙诈与亡孰愈?'曰:‘亡愈。'”故复发此问。“周也羊,秦也狼”者,国策 楚策云:“夫秦虎狼之国也。”“然则狼愈与”者,既无许周之文,故更疑强胜于 弱也。“羊、狼一也”者,宋云:“言周以不道而弱,秦以不道而强,强与弱虽异, 而不道一也。” 或问:“蒙恬忠而被诛,忠奚可为也?”曰:“堑山堙谷,起临洮,击辽水, 力不足而死有余,忠不足相也。”〔注〕相,助也。虽尽一身之节,而残百姓之命, 非所以务民之义。〔疏〕“蒙恬忠而被诛”者,蒙恬列传云:“蒙恬者,其先齐人 也。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,官至上卿。骜子武,武子曰恬,蒙恬弟毅。始皇二 十六年,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,攻齐,大破之,拜为内史。秦已幷天下,乃使蒙恬 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,收河南,筑长城。因地形用险制塞,起临洮,至辽东,延袤 万余里。于是渡河据阳山,逶蛇而北,暴师于外十余年,居上郡。是时蒙恬威振匈 奴,始皇甚尊宠蒙氏,信任贤之而亲近。蒙毅位至上卿,恬任外事,而毅常为内谋, 名为忠信。故虽诸将相,莫敢与之争焉。始皇欲游天下,道九原,直抵甘泉。乃使 蒙恬信道,自九原抵甘泉,堑山堙谷,千八百里,道未就。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 会稽,并海上,北走琅邪。道病,使蒙毅还祷山川。未反,始皇至沙丘崩。中车府 令赵高乃与丞相李斯、少子胡亥阴谋,立胡亥为太子。太子已立,遣使者以罪赐公 子扶苏、蒙恬死。扶苏已死,蒙恬疑而复请之。使者还报。毅还至,赵高因为胡亥 忠计,欲以灭蒙氏。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,前已囚蒙恬于阳周。丧至咸阳,已葬, 太子立,为二世皇帝。而赵高亲近,日夜毁恶蒙氏。胡亥令蒙毅曰:‘先主欲立太 子,而卿难之,今丞相以卿为不忠,罪及其宗。朕不忍,乃赐卿死,亦甚幸矣。' 遂杀之。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,令蒙恬曰:‘君之过多矣,而卿弟毅有大罪,法及 内史。'恬曰:‘自吾先人及至子孙,积功信于秦三世矣。今臣将兵三十余万,身 虽囚系,其势足以倍畔。自知必死而守义者,不敢辱先人之教,以不忘先主也。恬 之宗世无二心,而事卒如此,是必孽臣逆乱,内陵之道也。'使者曰:‘臣受诏行 法于将军,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。'蒙恬喟然太息曰:‘我何罪于天,无过而死 乎!'良久,徐曰:‘恬罪固当死矣。起临洮,属之辽东,城堑万余里,此其中不 能无绝地脉哉,此乃恬之罪也。'乃吞药自杀。”“堑山堙谷”者,音义:“堑山, 七艳切。”按:世德堂本作“堑”。说文:“堑,坑也。”堑即堑之别体,史记亦 作“堑”。说文:“垔,塞也。”俗字作“湮”。“起临洮,击辽水”者,音义: “临洮,音叨(一)。”按:地理志:“陇西郡临洮,洮水出西羌中,北至抱罕, 东入河。禹贡西倾山在县西(二),南部都尉治也。今甘肃巩昌府岷州,秦长城起 州西。秦校云:“‘击'当作‘系'。系,属也。史记云属之辽东,不作‘击', 可知。但各本皆误,或治平初刻已如此。”俞云:“击字无义,疑‘罄'字之误。 尔雅释诂:‘罄,尽也。'言起临洮,而尽辽水也。史记作‘起临洮,至辽东', ‘至'即尽义。”按:秦说是也。地理志:“辽东郡望平,大辽水出塞外,南至安 市入海,行千二百五十里。”按:今辽河有东、西二源,自边外合流而南,径开原、 铁岭县西,又径承德、辽阳、海城之西,又南入海。“力不足而死有余”,司马依 宋、吴本,“死”作“尸”。俞云:“力者,功也。周官司勋‘治功曰力',是也。 言蒙恬为秦筑长城,无救于秦之亡,以论功则不足,以致死则有余矣。故曰力不足 而死有余。宋、吴本‘死'作‘尸',误也。温公从之,非是。”按:宋、吴本固 非,俞义亦未安。力不足而死有余,谓用民之力而不惜民之死,民力匮而死者多耳。 太史公曰:“吾适北边,自直道归,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,堑山堙谷,通直 道,固轻百姓力矣。夫秦之初灭诸侯,天下之心未定,痍伤者未瘳,而恬为名将, 不以此时强谏,振百姓之急,养老存孤,务修众庶使之和,而阿意兴功,此其兄弟 遇诛,不亦宜乎!”即此文之义。忠不足相也,音义:“相,息亮切。”按:“相” 疑“称”之驳文,传写误耳。注“相,助也”。按:俞云:“说文木部:‘相,省 视也,从目从木,易曰:地可观者,莫可观于木。'是相与观义近。忠不足相也, 犹曰忠不足观也。不曰观而曰相,子云好为艰深之辞故耳。李注训相为助,将谁使 助之乎?失杨旨矣。”荣按:弘范以相为助,犹云赞也,义虽稍纡,然固可通。曲 园训为观,而以此为子云好作艰深之辞,尤谬。(一)“叨”字原本作“洮”,音 近,且涉上文“临洮”而讹,今据音义改。(二)“西”下原本有偏书小字“句”, 盖作者以示句读,今删。 或问:“吕不韦其智矣乎,以人易货?”〔注〕吕不韦,阳翟贾人也,出千金 以助子楚,子楚既立,不韦相之。曰:“谁谓不韦智者与?以国易宗。〔注〕虽开 列封,先笑后愁;身既鸩死,宗族窜流。不韦之盗,穿窬之雄乎?〔注〕不以其道, 非盗如何?穿窬也者,吾见担石矣,未见雒阳也。”〔注〕雒阳,不韦所国地也。 揭雒阳而行天下,岂徒担石乎?〔疏〕“吕不韦其智矣乎?以人易货”者,吕不韦 列传云:“吕不韦者,阳翟大贾人也,往来贩贱卖贵,家累千金。秦昭王太子死, 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。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,中男名子楚,(按:本名异人。) 为秦质子于赵,车乘进用不饶,居处困不得志。吕不韦贾邯郸,见而怜之,曰: ‘此奇货可居。'乃往见子楚,说曰:‘秦王老矣,安国君得为太子。窃闻安国君 爱幸华阳夫人。华阳夫人无子,能立适嗣者,独华阳夫人耳。子贫,客于此,非有 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。不韦虽贫,请以千金为子西游,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,立 子为适嗣。'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,结宾客。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,自奉 而西游秦,求见华阳夫人姊,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。因言子楚贤智,日夜泣思太 子及夫人。夫人大喜,承太子闲,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,来往者皆称誉之,妾 不幸无子,愿得子楚,立以为适嗣,以托妾身。安国君许之。秦昭王五十年,使王 齮围邯郸急,赵欲杀子楚。子楚与吕不韦谋,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,得脱,亡赴秦 军,遂以得归。秦昭王五十六年薨,太子安国君立为王,华阳夫人为王后,子楚为 太子。秦王立一年薨,谥为孝文王。太子子楚代立,是为庄襄王。以吕不韦为丞相, 封为文信侯,食河南洛阳十万户。”此以人易货之事。传“奇货可居”下集解云: “以子楚方财货也。”正义引战国策(按:秦策文。)云:“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, 见秦质子异人,归谓其父曰:‘耕田之利几倍?'曰:‘十倍。'‘珠玉之赢几倍?' 曰:‘百倍。'‘立主定国之赢几倍?'曰:‘无数。'不韦曰:‘今力田疾作, 不得暖衣饱食;今定国立君,泽可遗后世,愿往事之。'”是其义也。“谁谓不韦 智者与?以国易宗”者,传又云:“庄襄王三年薨,太子政立为王,尊吕不韦为相 国,号仲父。始皇九年,有告嫪毐常与太后私乱,事连相国吕不韦。九月,夷嫪毐 三族。十年十月,免相国吕不韦,就国河南。岁余,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,请文 信侯。秦王恐其为变,乃赐文信侯书曰:‘君何功于秦?秦封君河南,食十万户。 君何亲于秦?号称仲父。其与家属徙处蜀。'吕不韦自度稍侵,恐诛,乃饮酖而死。” 此以国易宗之事。国谓雒阳。以国易宗,谓得雒阳之封,而终乃身诛而家族徙也。 “不韦之盗”,世德堂本作“吕不韦之盗”。“穿窬之雄乎”者,音义:“窬,音 踰。”论语云:“色厉而内荏,譬诸小人,其犹穿窬之盗也与!”孔注云:“穿, 穿壁也;窬,窬墙也。”皇疏云:“窬,窦也。”“吾见担石矣,未见雒阳也”者, 音义:“担石,都滥切,又都甘切。”按:说文:“儋,何也。”今字作“担荷”。 汉书蒯通传:“守儋石之禄者,阙卿相之位。”应劭云:“齐人名小罂为儋,受二 斛。”晋灼云:“石,斗石也。”颜云:“儋,音都滥反。或曰儋者,一人之所负 担也。”地理志云:“河南郡雒阳。”颜注引“鱼豢云:‘汉火德忌水,故去“洛” “水”,而加“隹”。如鱼氏说,则光武以后改为“雒”字也'。”说文“洛”篆 下段注云:“雍州洛水,豫州雒水,其字分别,自古不紊。许书水部下不举豫州水, 尤为二字分别之证。后人书豫水作‘洛',其误起于魏。裴松之引魏略曰:‘黄初 元年,诏以汉火行也,火忌水,故洛去水而加隹。魏于行次为土,土,水之牡也, 水得土而乃流,土得水而柔,故除隹而加水,变雒为洛。'此丕妄言,以揜己纷更 之咎,且自诡于复古。自魏至今,皆受其欺。”又“雒”篆下注云:“自魏黄初以 前,伊、雒字皆作此,与雍渭、洛字迥判。”汪氏之昌青学斋集云:“洛水有二原, 只作‘洛',其作‘雒'者,假借字。文选江赋:‘聿经始于洛、汭。'李善注: ‘洛与雒通。'恐亦古有其说。就汉碑考之,孔龢碑‘奏雒阳宫',韩敕碑‘河南 雒阳史晨奏铭钩河擿雒',此皆假‘雒'为‘洛';袁良碑‘隐居河、洛',仍作 ‘洛'字。说文羽部‘翚'注:‘一曰伊、雒而南,雉五釆皆备曰翚。'隹部则云: ‘伊、洛而南曰翚。'一作雒,一作洛,尤雒、洛两字容得通假之一证。以例经传 之伊、雒,则古不必定作‘伊、雒'也。”按:托名■帜,本无正字,伊、雒虽水 名,其文不必皆从水。古“伊、雒”字作“雒”者,所以别于“渭、洛”之“洛”, 不得以“洛”为正,而“雒”为假也。雒阳故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阳县东北二十里。 秦本纪:“昭襄王五十一年,秦使将军摎攻西周,西周君走来自归,顿首受罪,尽 献其邑三十六城,口三万。”又:“庄襄王元年,东周君与诸侯谋秦,秦使相国吕 不韦诛之,尽入其国。秦界至大梁,初置三川郡。”集解引“韦昭云:‘有河、洛、 伊,故曰三川。'骃按:地理志,汉高祖更名河南郡。”则庄襄王时尽有东、西周 地,故得以雒阳为不韦封国也。吴云:“穿窬者伺慢藏,而得之不过一担一石,而 不韦伺人颜色,而取雒阳之封,是其雄也。”注“吕不韦,阳翟贾人也”。按:此 本史记列传。彼索隐云:“翟,音狄,俗又音宅。地理志:县名,属颍川。战国策 以不韦为濮阳人,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。班固虽云太史公据战国策,然为此 传当别有所闻见,故不全依彼说。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易彼书,遂令不 与史迁记合也。”荣按:阳翟,战国时为韩都,今河南开封府。禹州治濮阳,为卫 都,今直隶大名府开州西南。史称不韦“阳翟大贾”,不云“阳翟人”,则不韦乃 卫人而贾于韩者。国策就生地言,史记就贾地言,本无不合。至事迹偶有异同,则 史公齐整百家,不必专采一书,刘子政校书,必无据异闻改易正文之理。司马贞说 殊谬。注“虽开”至“窜流”。按:世德堂本“开”误“闻”,此弘范以列封字释 国,谓不韦得雒阳之封而陨其宗也。吴云:“徼取国权,以易宗族。”司马云: “贪国权而丧其宗。”则皆以国为国权,与弘范义异。班孟坚答宾戏云:“吕行诈 以贾国,秦货既贵,厥宗亦坠。”语意本此。似孟坚解“以国易宗”亦与司封、温 公同。注“非盗如何”。按:治平本作“何如”,今依世德堂本。如之为言,而也。 非盗如何,犹云非盗而何。学行注云:“卖者欲贵,买者欲贱,非异如何?”问明 注云:“人所不能,非难如何?”孝至注云:“自然之美,非至如何?”文义并同。 注“雒阳”至“石乎”。按:秦策云:“子楚立,以不韦为相,号曰文信侯,食蓝 田十二邑。”盖初封蓝田,及秦使不韦灭东周,乃以雒阳为其封国也。庄子胠箧释 文引三苍:“揭,举也,儋也,负也。”小尔雅广言:“荷,揭担也。”揭雒阳而 行天下,喻以雒阳为担石也。 “秦将白起不仁,奚用为也?”“长平之战,四十万人死,蚩尤之乱,不过于 此矣。原野猒人之肉,川谷流人之血,将不仁,奚用为!”〔注〕奚,何。“翦?” 〔注〕问王翦何将也。曰:“始皇方猎六国,而翦牙欸。”〔注〕咀噬用牙,言其 酷也。欸者,绝语,叹声。〔疏〕“秦将白起”者,音义:“秦将,子亮切,下同。” 按:白起王翦列传云:“白起者,郿人也,善用兵,事秦昭王。昭王十三年,为左 庶长。其明年,为左更,迁为国尉。明年,为大良造。后迁为武安君。四十八年, 韩、赵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:‘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,南定鄢、 郢、汉中,北禽赵括之军,虽周、召、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。今赵亡,秦王王,则 武安君必为三公,君能为之下乎?'于是应侯言于秦王,许韩、赵之割地以和,且 休士卒。正月,皆罢兵。武安君闻之,由是与应侯有隙。其九月,秦复使王陵攻赵。 四十九年正月,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,武安君终辞不肯行,遂称病。秦围邯郸不能 拔,军多失亡,秦王强起武安君。武安君遂称病笃,应侯请之不起,于是免武安君 为士伍,迁之阴密。武安君病未能行,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。武安君既 行,至杜邮,秦昭王与应侯、群臣议曰:‘白起之迁,其意尚怏怏不服,有余言。' 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,武安君遂自杀。武安君之死也,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(一)。 死而非其罪,秦人怜之,乡邑皆祭祀焉。”“长平之战,四十万人死”者,列传云: “四十七年,秦使王龁攻韩,取上党,上党民走赵。赵军长平,龁因攻赵。赵使廉 颇将,廉颇坚壁以待秦,秦数挑战,赵兵不出。赵王数以为让,而秦相应侯又使人 行千金于赵为反间,曰:‘秦之所畏,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,廉颇易与,且降矣。' 赵王因使赵括代廉颇将,以击秦。秦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。赵括至则出兵击 秦军,秦军详败而走。赵军逐胜,追造秦壁。壁坚,拒不得入,而秦奇兵二万五千 人绝赵军后,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。赵军分而为二,粮道绝,而秦出轻兵击之, 赵战不利,因筑壁坚守,以待救至。秦王闻赵食道绝,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,遮 绝赵救及粮食,至九月,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,皆内阴相杀食。赵括出锐卒自搏战, 秦军射杀赵括,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。武安君计曰:‘前已拔上党,上党民 不乐为秦而归赵,赵卒反复,非尽杀之,恐为乱,乃挟诈而尽坑杀之,遗其小者二 百四十人归赵。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,赵人大震。”彼集解云:“长平在泫氏。” 索隐云:“地理志泫氏在上党郡也。”正义云:“长平故城在泽州高平县西北一里 也。”水经注沁水篇引上党记云:“长平城在郡之南,秦垒在郡之西,二军共食流 水,涧相去五里。秦坑赵众,收头颅筑台于垒中,因山为台,崔嵬桀起,今仍号之 曰白起台。城之左右沿山亘堤,南北五十许里,东西二十余里,悉秦、赵故垒,遗 壁旧存焉。”按:上党,今山西泽州府地;泫氏,今泽州府高平县。长平故城,在 县西北。四十万人死,后汉书班固传章怀太子注引作“坑四十万人”,文选班孟坚 东都赋李注引与今各本同。“蚩尤之乱,不过于此矣”者,吕刑云:“蚩尤惟始作 乱,延及于平民。”五帝本纪云:“轩辕之时,神农氏世衰,蚩尤最为暴,莫能伐。 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,三战然后得其志。蚩尤作乱,不用帝命,于是黄帝乃征 师诸侯,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,遂禽杀蚩尤。”正义引龙鱼河图云:“黄帝摄政, 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,并兽身人语,铜头铁额,食沙,造五兵仗,刀戟大弩,威振 天下。”“原野猒人之肉,川谷流人之血”者,说文:“猒,饱也。从甘,从●。” 会意,甘亦声。古书多以“厌”为之。东都赋用此语,后汉书班固传作“猒”,章 怀注引法言同,明旧本法言如此。世德堂本作“厌”,文选及李注引法言同。盖校 书者以少见“猒”字改之。国策秦策云:“白起北坑马服,诛屠四十余万之众,流 血成川,沸声若雷。”“将不仁,奚用为”者,司马云:“用将所以救乱诛暴。” 是也。“翦”者,史记王翦与白起同传,故因论起而遂及翦也。列传云:“王翦者, 频阳东乡人也,少而好兵,事秦始皇。始皇十八年,翦将攻赵,岁余,遂拔赵,赵 王降,尽定赵地为郡。明年,秦王使王翦攻燕,燕王喜走辽东,翦遂定燕、蓟而还。 秦始皇既灭三晋,走燕王,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击荆,大破荆军,至蕲南,杀其将 项燕,荆兵遂败走,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。岁余,虏荆王负刍,竟平荆地为郡县。” “始皇方猎六国,而翦牙”者,王翦与其子贲同时为秦将,六国表始皇十九年,王 翦拔赵,虏王迁;二十二年,王贲击魏,得其王假,尽取其地;二十四年,王翦、 蒙武破楚,虏其王负刍;二十五年,王贲击燕,虏王喜;二十六年,王贲击齐,虏 王建,初幷天下。总核六国,惟韩为内史胜所灭,其余五国悉见灭于王翦父子,故 太史公云:“王翦为秦将,夷六国。”是始皇为虎狼,而翦为之牙也。音义:“牙 欸,乌开切,又许介切。”按:说文:“欸,訾也。”朱氏通训定声云:“实与 ‘诶'同字。”按:说文:“诶,可恶之词也。”苍颉训诂:“欸,恚声也。”亦 以“欸”为之,今犹有此语。南人读乌开切,音如哀;北人读许介切,音如●也。 注“欸者,绝语,叹声”。按:弘范读欸单字为句,不与上文相连。音义出“牙欸”, 乃摘正文二字为识,非以牙欸连读。吴云:“牙欸,谓切齿而怒也。”失之。(一) “月”下原本有偏书小字“句”,盖作者以示句读,今删。 或问:“要离非义者与?不以家辞国。”曰:“离也,火妻灰子,以求反于庆 忌,实蛛蝥之靡也,焉可谓之义也?”〔注〕义者,臣子死节乎君亲之难也。离由 平人而焚烧妻、子,诈为吴雠,求信于庆忌,反而刺之,若蜘蛛之小巧耳。“政?” 〔注〕问聂政。“为严氏犯韩,刺相侠累,曼面为姊,实壮士之靡也,焉可谓之义 也?”〔注〕侠累,韩相名也。“轲?”〔注〕问荆轲。“为丹奉于期之首、燕督 亢之图,入不测之秦,实刺客之靡也,焉可谓之义也?”〔注〕三士所死,皆非君 亲之难也。非义之义,君子不为也。〔疏〕“要离非义者与?不以家辞国”者,音 义:“要离,一遥切。”吕氏春秋忠廉云:“吴王欲杀王子庆忌,而莫之能杀,吴 王患之。要离曰:‘臣能之。'吴王曰:‘汝恶能乎?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,而 不能及;射之矢,左右满把,而不能中。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,上车则不能登轼, 汝恶能?'要离曰:‘士患不勇耳,奚患于不能?王诚能助,臣请必能。'”高注 云:“吴王阖闾先篡庶父僚,而即其位。庆忌者,僚之子也,故欲杀之。庆忌有力 捷疾而人皆畏之,无能杀之者。”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云:“要离曰:‘臣国东千里 之人,臣细小无力,迎风则僵,负风则伏,大王有命,臣敢不尽力。'王曰:‘庆 忌明智之人,归穷于诸侯,不下诸侯之士。'要离曰:‘臣闻安其妻子之乐,不尽 事君之义,非忠也;怀室家之爱,而不除君之患者,非义也。臣诈以负罪出奔,愿 王戮臣妻、子,断臣右手,庆忌必信臣矣。'”此不以家辞国之事。“离也,火妻 灰子,以求反于庆忌”者,音义:“求反,俗本脱‘求'字。”按:世德堂本无 “求”字。公羊传哀公篇:“其易奈何?诈反也。”解诂云:“反,报也。”求反 于庆忌,谓求报偿其火妻灰子之事于庆忌之身也。忠廉云:“吴王曰:‘诺。'明 旦,加要离罪焉,挚执妻、子而焚之,扬其灰。要离走,往见王子庆忌于卫。王子 庆忌喜曰:‘吴王之无道也,子之所见也,诸侯之所知也。今子得免而去之,亦善 矣。'要离与王子庆忌居,有间,谓王子庆忌曰:‘吴之无道也愈甚,请与王子往 夺之国。'王子庆忌曰:‘善。'乃与要离俱涉于江,中江,拔剑以刺王子庆忌。” 毕氏沅校云:“左氏哀二十年,传云:‘庆忌适楚。'此与吴越春秋皆云在卫。” 荣按:阖闾内传云:“庆忌死,要离渡至江陵,愍然不行,遂投身于江。未绝,从 者出之。要离乃自断手足,伏剑而死。”若自卫返吴,不得远经江陵,当依左传作 在楚也。“实蛛蝥之靡也”者,音义:“蛛蝥,俗本作‘蛛螫',误。贾谊新书曰: ‘蛛蝥作网。'蝥,音矛。”按:新书礼篇文。“蛛”亦作“■”。方言:“■■, ■蝥也。”“靡”治平本作“劘”,钱本同。秦校云:“‘劘'当作‘靡'。”按: 下文壮士之靡、刺客之靡,字皆作“靡”,此不当歧出。世德堂本作“靡”,今据 改。俞云:“靡与为古音相近,故广雅释诂云:‘靡,为也。'蛛蝥之靡即蛛蝥之 为,犹曰是乃蛛蝥之所为耳。下文两‘靡'字义同。”舍弟东宝云:“左太冲吴都 赋:‘其邻则有任侠之靡,轻訬之客。'刘注‘靡,美也',引法言‘刺客之靡'。 靡、美声义略近,凡训美善者,皆有雄长之义。广雅:‘英,美也。'王氏疏证引 ‘百人曰俊,千人曰英'。然则蛛蝥之靡犹云蛛蝥之雄,与上文穿窬之雄,下文滑 稽之雄同义。”按:东说是也。靡、美一声之转。“政”世德堂本作“政也”。按: 刺客列传云:“聂政者,轵深井里人也。”“为严氏犯韩,刺相侠累,曼面为姊” 者,音义:“为严,于伪切。下‘为姊'、‘为丹'同。刺相,息亮切,下‘董相' 同。曼面,谟官切,涂面。”按:列传云:“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,与韩相侠累有 郄,严仲子恐诛,亡去,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。至齐,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,避 仇隐于屠者之间。严仲子至门,奉黄金百镒,前为聂政母寿。聂政惊怪其厚,固谢 严仲子。严仲子辟人,因为聂政言曰:‘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,然至齐,窃闻足 下义甚高,故进百金者,将用为大人麤粝之费,得以交足下之驩,岂敢以有求望邪?' 聂政曰:‘臣所以降志辱身,居市井屠者,徒幸以养老母。老母在,政身未敢以许 人也。'严仲子固让,聂政竟不敢受也。久之,聂政母死。既已葬,除服,乃遂西 至濮阳,见严仲子曰:‘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,徒以亲在。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, 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,请得从事焉。'严仲子具告之,曰:‘臣之仇韩相侠累,累 又韩君之季父也,宗族甚多,居处兵卫甚设,臣欲使人刺之,众终莫能就。今足下 幸而不弃,请益其车骑、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。'聂政曰:‘韩之于卫,相去中间 不甚远,今杀人之相,相又国君之亲,此其势不可以多人。'遂谢车骑、人徒,独 行仗剑至韩。韩相侠累方坐府上,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。聂政直入上阶,刺杀侠累, 左右大乱。聂政大呼,所击杀者数十人。因自皮面、抉眼,自屠出肠,遂以死。韩 取聂政尸暴于市,购问莫知谁子。政姊荣闻人有刺韩相者,乃于邑曰:‘其是吾弟 与?'立起如韩之市,而死者果政也。伏尸哭极哀,曰:‘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 也。严仲子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,士为知己者死。今乃以妾尚在之故,重自刑 以绝从。(索隐:“从,音踪。”)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诛,灭贤弟之名?'大惊韩 市人,乃大呼天者三,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。”索隐引高诱云:“严遂,字仲子。” 又云:“按表,聂政杀侠累在列侯三年。列侯生文侯,文侯生哀侯,凡更三代。哀 侯六年为韩严所杀,今言仲子事哀侯,恐非其实。”按:事亦见国策韩策,在烈侯 时。严仲子,策作“严遂”;侠累,策作“傀”;姊荣,策作“嫈”。俞云:“曼 当读为镘。尔雅释宫:‘镘谓之杇。'说文木部:‘杇,所以涂也。'是镘者,所 以涂之具,故涂即谓之镘。镘面者,涂面也。音义说得之。”按:传作“皮面”, 韩策同,盖“柀”之假。说文:“柀,析也。”谓破析其面,不欲令人识之。此云 曼面者,曼谓曼漶。子云自序云:“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。”张晏云:“曼,音满。” 颜云:“曼漶,不分别貌。”是也。“轲”世德堂本作“轲也”。按:荆轲见前。 “为丹奉于期之首、燕督亢之图,入不测之秦”者,音义:“督亢,音刚。”刺客 列传云:“荆轲既至燕,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。秦日出兵山东,以伐齐、楚、三 晋,稍蚕食诸侯,且至于燕。燕君臣皆恐祸之至,太子丹患之,问其傅鞠武,武对 曰:‘请入图之。'居有间,秦将樊于期得罪于秦王,亡之燕,太子受而舍之。鞠 武谏曰:‘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。请西约三晋,南连齐、楚,北购于单 于,(索隐:“购,读与‘媾'同。”)其后乃可图也。'太子曰:‘太傅之计, 旷日弥久,心惛然,恐不能须臾。愿太傅更虑之。'鞠武曰:‘燕有田光先生,其 为人智深而勇沉,可与谋。'太子曰:‘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。'田光乃造焉。 太子避席而请曰:‘燕、秦不两立,愿先生留意也。'田光曰:‘虽然,光不敢以 图国事。所善荆卿,可使也。'太子曰:‘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。'荆轲遂见太 子,太子避席顿首,曰:‘今秦有贪利之心,而欲不可足也。非尽天下之地,臣海 内之王者,其意不厌。燕小弱,数困于兵,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,诸侯服秦,莫敢 合从。丹之私计,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,劫秦王,使悉反诸侯侵地,若曹 沫之与齐桓公,则大善矣。则不可,因而刺杀之。彼秦大将擅兵于外,而内有乱, 则君臣相疑。以其间诸侯得合从,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愿,而不知所委命,唯荆 卿留意焉。'荆轲许诺。久之,秦将王翦破赵,虏赵王,尽收入其地。进兵北略地, 至燕南界。太子恐惧,乃请荆轲曰:‘秦兵旦暮渡易水,则虽欲长侍足下,岂可得 哉?'荆轲曰:‘微太子言,臣愿谒之。今行而毋信,则秦未可亲也。夫樊将军, 秦王购之金千斤,邑万家,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,奉献秦王,秦王必说见 臣,臣乃得有以报太子(一)。'乃遂私见樊于期曰:‘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, 报将军之仇者,何如?'于期乃前曰:‘为之柰何?'荆轲曰:‘愿得将军之首以 献秦王,秦王必喜而见臣,臣左手把其袖,右手揕其胸,然则将军之仇报,而燕见 陵之愧除矣。'樊于期遂自刭。太子闻之驰往,既已不可柰何,乃遂盛樊于期首函 封之。燕国有勇士秦舞阳,年十三,杀人,(当重“人”字,燕策可证。)不敢忤 视,乃令秦舞阳为副。于是荆轲遂至秦,持千金之资币物,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 嘉。嘉为先言于秦王,秦王大喜,乃朝服,设九宾,见燕使者咸阳宫。荆轲奉樊于 期头函,而秦舞阳奉地图匣,以次进。轲既取图奏之,秦王发图,图穷而匕首见, 因左手把秦王之袖,而右手持匕首揕之。未至身,秦王惊,自引而起,袖绝,拔剑, 剑长操其室,不可立拔。荆轲逐秦王,秦王环柱而走。左右乃曰:‘王负剑!'负 剑,遂拔以击荆轲,断其左股。荆轲废,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,不中,中铜柱。秦 王复击轲,轲被八创,于是左右既前杀轲。秦王大怒,益发兵诣赵,诏王翦军以伐 燕。后五年,秦卒灭燕。”按:亦见国策燕策。樊于期,武梁祠画象作“樊于其”。 列传集解引“徐广云:‘方城县有督亢亭。'骃按:刘向别录曰:‘督亢,膏腴之 地。'”索隐引司马彪郡国志云:“蓟县方城有督亢亭。”正义云:“督亢坡在幽 州范阳县东南十里,今固安县南有督亢陌,幽州南界。”燕世家集解云:“督亢之 田在燕东,甚良沃,欲献秦,故画其图而献焉。”水经注巨马水篇云:“巨马水又 东径督亢泽,泽苞方城县,县故属广阳,后隶于涿。郡国志曰:‘县有督亢亭。' 孙畅之述画有督亢地图,言燕太子丹使荆轲赍入秦,秦王杀轲,图亦绝灭。”按: 方城故城在今顺天府固安县南。入不测之秦,用荆轲语,彼传云“提一匕首,入不 测之强秦”也。注“若蜘蛛之小巧耳”。按:治平本“小巧”上有“虫”字,衍也; 钱本无,世德堂本亦无。弘范训靡为细,故云尔。小尔雅广言:“靡,细也。”然 壮士之靡、刺客之靡似不得训为细,则此注亦未安也。”注“问聂政”。按:世德 堂本无此注。注“侠累,韩相名”。按:广韵“侠”字注云:“任侠。又姓,战国 策有韩相侠累。”则以侠为姓,然侠累,韩君之季父,侠非其姓可知。或侠累之后 以侠为氏耳。又韩策作“傀”,广韵误以史记为国策也。韩非子内储说作“廆”, 即“傀”之异文。侠累之“侠”,索隐音古挟反,则与任侠字异读。疑侠累为廆, 犹寿梦为乘之比,急言之曰傀,曰廆,缓言之曰侠累耳。古今人表作“侠絫”。注 “非义之义,君子不为也”。按:孟子云:“非礼之礼,非义之义,大人弗为。” (一)“子”下原本有偏书小字“句”,盖作者以示句读,今删。 或问:“仪、秦学乎鬼谷术,而习乎纵横言,安中国者各十余年,是夫?”曰: “诈人也,圣人恶诸。”曰:“孔子读,而仪、秦行,何如也?”〔注〕欲读仲尼 之书,而行苏、张之辩。曰:“甚矣!凤鸣而鸷翰也。”“然则子贡不为与?” 〔注〕言子贡亦行游说,抑齐、破吴以救鲁。曰:“乱而不解,子贡耻诸;说而不 富贵,仪、秦耻诸。”〔注〕耻国乱而不解,于义高;耻游说而不富贵,其情下。 〔疏〕“仪、秦学乎鬼谷术,而习乎纵横言”者,张仪列传云:“张仪者,魏人也, 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,苏秦自以不及张仪。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。苏秦已 说赵王而得相(一),约从亲。张仪乃遂入秦,惠王以为客卿,与谋伐诸侯。秦惠 王十年,仪言秦复与魏,而使公子繇质于魏。仪因说魏王入上郡、少梁谢秦惠王, 惠王乃以张仪为相。仪相秦四岁,立惠王为王。居一岁,为秦将取陕,筑上郡塞。 其后二年,免相,相魏以为秦,欲令魏先事秦,而诸侯效之。魏王不肯听。留魏四 岁而魏襄王卒,哀王立。张仪复说哀王,哀王不听。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,张仪复 说魏王事秦,哀王乃倍从约,而因仪请成于秦。张仪归,复相秦。三岁而魏复背秦 为从,秦攻魏,取曲沃。明年,魏复事秦。秦欲伐齐,齐、楚从亲,于是张仪往相 楚,说楚王闭关绝约于齐,请献商、于之地六百里,秦、楚长为兄弟之国。楚王大 说而许之,遂闭关绝约于齐,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。齐王大怒,折节而下秦,秦、 齐之交合。张仪乃谓楚使者曰:‘臣有奉邑六里,愿以献大王左右。'楚使者还报 楚王,楚王大怒,发兵而攻秦,秦、齐兵共攻楚,斩首八万。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, 至蓝田大战,楚大败,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。秦要楚,欲得黔中地,欲以武关外 易之。楚王曰:‘不愿易地,愿得张仪,而献黔中地。'张仪乃请行,曰:‘臣善 靳尚,尚得事楚夫人郑袖,袖所言皆从。且臣奉王之节使楚,楚何敢加诛?假令诛 臣,而为秦得黔中之地,臣之上愿。'遂使楚。楚怀王囚张仪,将杀之。于是郑袖 日夜言怀王,怀王后悔,赦张仪,厚礼之如故。张仪既出,未去,闻苏秦死,乃说 楚王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,楚太子入质于秦,长为昆弟之国,终身无相攻伐。于是 楚王卒许张仪与秦亲。张仪去楚,因遂之韩,说韩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。韩王听仪 计。张仪归报,秦惠王封仪五邑,号曰武信君。使张仪东说齐愍王事秦,齐王曰: ‘齐僻陋,隐居东海之上,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。'乃许张仪。张仪去,西说赵王 曰:‘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,而韩、梁称为东藩之臣,齐献鱼盐之地,臣窃为大王 计,莫如与秦王遇于渑池,面相见而口相结,请案兵无攻。'赵王许张仪。张仪乃 去,北之燕,说燕昭王曰:‘今赵王已入朝渑池,效河间以事秦。今大王不事秦, 秦下甲云中、九原,驱赵而攻燕,则易水、长城非大王之有也。'燕王听仪。仪归 报,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。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,及即位,群臣多谗张仪。张 仪惧诛,乃因谓秦武王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。秦王乃具革车三十乘,入仪之梁。张 仪相魏一岁,卒于魏也。”索隐云:“年表云张仪以安王十年卒,纪年云梁哀王九 年五月卒。”苏秦列传云:“苏秦者,东周雒阳人也,东事师于齐,而习之于鬼谷 先生。出游数岁,大困而归。出其书遍观之,得周书阴符,伏而读之。期年,求说 周显王,显王弗信。乃西至秦,说惠王。秦王方诛商鞅,疾辩士弗用。乃东至赵, 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,号奉阳君。奉阳君弗说之,去游燕,岁余而后得见,说燕文 侯与赵从亲。文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,而奉阳君死,即因说赵肃侯一韩、魏、 齐、楚、燕、赵以从亲,以畔秦,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,通质,刳白马而盟。 诸侯有不如约者,以五国之兵共伐之,六国从亲以宾秦,(按:宾读为“摈”。) 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,以害山东矣。赵王乃饰车百乘,黄金千镒,白璧百双,锦 绣千纯,以约诸侯。于是说韩宣王,又说魏襄王,因东说齐宣王,西南说楚威王 (二),六国从合而幷力焉。苏秦为从约长,幷相六国。北报赵王,赵肃侯封为武 安君,乃投从约书于秦,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。其后秦使犀首欺齐、魏与共伐 赵,欲败从约。齐、魏伐赵,赵王让苏秦,苏秦恐,请使燕,必报齐。苏秦去赵而 从约皆解。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。文侯卒,太子立,是为燕易王。易王初立, 齐宣王因燕丧伐燕,取十城。苏秦大惭,曰:‘请为王取之。'苏秦见齐王,于是 乃归燕之十城。人有毁苏秦者,曰:‘左右卖国,反复之臣也,将作乱。'苏秦恐 得罪,归,燕王益厚遇之。易王母,文侯夫人也,与苏秦私通,苏秦恐诛,乃说燕 王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。齐宣王以为客卿。齐宣王卒,愍王即位,说愍王厚葬以 明孝;高宫室,大苑囿,以明得意。欲破敝齐而为燕。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, 而使人刺苏秦,不死,殊而走。苏秦且死,乃谓齐王曰:‘臣即死,车裂臣以■于 市,曰:苏秦为燕作乱于齐。如此,则臣之贼必得矣。'于是如其言,而杀苏秦者 果自出,齐王因而诛之。”集解于“习之于鬼谷先生”下引徐广云:“颍川阳城有 鬼谷,盖是其人所居,因为号。”又引风俗通义云:“鬼谷先生,六国时从横家。” 索隐云:“鬼谷,地名也。扶风池阳、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,盖是其人所居,因为 号。又乐台注鬼谷子书云:‘苏秦欲神秘其道,故假名鬼谷。'”按:今河南河南 府登封县东南有鬼谷。“纵横”古书多作“从横”,或作“从衡”。淮南子览冥云: “晚世之时,七国异族,诸侯制法,各殊习俗,纵横间之,举兵而相角。”高注云: “苏秦约从,张仪连横,南与北合为从,西与东合为横。”周本纪:“西周恐,倍 秦与诸侯约从。”集解引文颍云:“关东为从,关西为横。”又引孟康云:“南北 为从,东西为横。”又引臣瓒云:“以利合为从,以威势相胁曰横。”正义云: “按:诸说未允。关东地南北长,长为从,六国共居之;关西地东西广,广为横, 秦独居之。”汉书艺文志有苏子三十一篇、张子十篇,今并不存。“诈人也,圣人 恶诸”者,张仪列传云:“太史公曰:‘三晋多权变之士,夫言从横强秦者,大抵 皆三晋之人也。夫张仪之行事,甚于苏秦,然世恶苏秦者,以其先死。而仪振暴其 短,以扶其说,成其衡道。要之,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!'”音义:“恶诸,乌路 切。”“孔子读,而仪、秦行”者,音义:“秦行,下孟切。‘美行'同。”按: 秦行之“行”,当读如字,说见问明“圣读庸行”疏。“凤鸣而鸷翰”者,音义: “鸷翰,胡安切,又侯旰切。”司马云:“鸷,鹰隼也;翰,羽翼也。”“然则子 贡不为与”者,此据弟子列传子贡传设难,言子贡即读孔子之书而为苏、张之祖者 也。世德堂本此句上有“曰”字。“乱而不解,子贡耻诸”者,论语云:“子贡问 曰:‘何如斯可谓之士矣?'子曰:‘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。'” 皇疏引李充云:“古之良使者,受命不受辞,事有权宜,则与时消息,排患释难, 解纷挫锐者,可谓良也。”即其义。“说而不富贵,仪、秦耻诸”者,音义:“说 而,失赘切。”按:苏秦列传云:“苏秦游数岁,大困而归,兄弟、嫂妹、妻妾窃 笑之。苏秦闻之而惭自伤,曰:‘夫士业已屈首受书,而不能以取尊荣,虽多亦奚 以为?”又云:“苏秦为从约长,幷相六国,北报赵王。乃行过雒阳,车骑辎重, 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,疑于王者。苏秦之昆弟、妻、嫂侧目不敢仰视,俯伏侍取食。 苏秦喟然叹曰:‘此一人之身,富贵则亲戚畏惧之,贫贱则轻易之,况众人乎?'” 又张仪列传云:“苏秦已说赵王,而得相约从亲,然恐秦之攻诸侯,败约后负,念 莫可使用于秦者,乃使人微感张仪曰:‘子始与苏秦善,今秦已当路,子何不往游 以求通子之愿?'张仪于是之赵上谒,求见苏秦。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,又使不 得去者数日。已而见之,坐之堂下,赐仆妾之食,因而数让之曰:‘以子之材能, 乃自令困辱至此,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,子不足收也。'谢去之。张仪之来也,自 以为故人求益,反见辱,怒,念诸侯莫可事,独秦能苦赵,乃遂入秦。”此皆仪、 秦以不富贵为耻之事。注“言子贡亦行游说,抑齐、破吴以救鲁”。按:世德堂本 “说”上无“行”字。弟子列传云:“田常欲作乱于齐,惮高、国、鲍、晏,故移 其兵,欲以伐鲁。子贡遂行至齐,说田常不如伐吴。田常曰:‘吾兵已加鲁矣,去 而之吴,大臣疑我,柰何?'子贡曰:‘君按兵无伐,臣请使吴王,令之救鲁而伐 齐,君因以兵迎之。'田常许之,使子贡南见吴王,说曰:‘救鲁,显名也;伐齐, 大利也,以抚泗上诸侯。名存亡鲁,实困强齐,智者不疑也。'吴王曰:‘越王苦 身养士,有报我心,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'子贡曰:‘置齐而伐越,则齐已平鲁矣。 夫伐小越而畏强齐,非勇也。且王必恶越,臣请东见越王,令出兵以从。'吴王大 悦,乃使子贡之越。越王遂问子贡,子贡曰:‘吴王为人猛暴,群臣不堪,国家敝 于数战,士卒弗忍,百姓怨上,大臣内变。今王诚发士卒佐之,其伐齐必也。彼战 不胜,王之福矣。战胜,必以兵临晋,臣请北见晋君,令共攻之,弱吴必矣。其锐 兵尽于齐,重甲困于晋,而王制其敝,此灭吴必矣。'越王大说,许诺。子贡遂行 报吴王。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。子贡因去之晋,谓晋君曰:‘齐与吴将战, 彼战而不胜,越乱之必矣。与齐战而胜,必以其兵临晋,修兵休卒以待之。'晋君 许诺。子贡去而之鲁,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,大破齐师,果以兵临晋,与晋人相 遇黄池之上。吴、晋争强,晋人击,大败吴师。越王闻之,涉江袭吴。吴王去晋而 归,与越战,不胜,越遂破吴。故子贡一出,存鲁,乱齐,破吴,强晋而霸越。子 贡一使,使势相破,十年之中,五国各有变。”司马云:“子贡存鲁,乱齐,破吴, 强晋,霸越,考其年与事皆不合,盖六国时游说之士托为之词。太史公不加考校, 因而记之,杨子亦据太史公书发此语。”梁氏志疑云:“子贡说齐、晋、吴、越一 节,家语屈节、越绝陈恒传、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并载之,昔贤历辩其谬。墨子非儒 下篇谓孔子怒晏子沮尼溪之封于景公,适齐欲伐鲁,乃遣子贡之齐,劝田常伐吴, 教高、鲍毋得害田常之乱,遂劝伐吴,三年之内,齐、吴破国。其为六国时之妄谈 可见,孔鲋诘墨辩之矣。或曰弟子传皆短简不繁,独子贡传榛芜不休,疑是后人阑 入,非史本文也。”荣谓史迁杂采百家,本多抵牾。子贡传之有此语,盖六国时盛 传之说,史迁因而收之,不必非史本文。至法言此文,乃或人据史记设难之辞,子 云但谓“乱而不解,子贡耻诸”,则即本论语“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”为义,非遂 信史记所载为真也。注“于义高”。按:世德堂本作“其义高”。(一)“相”下 原有偏书小字“句”,盖作者以示句读,今删。(二)“西”字原本作“东”,涉 上文“东说齐宣王”而讹,今据史记本传改。 或曰:“仪、秦其才矣乎?迹不蹈已。”〔注〕仪不迹秦。苏秦佩六国相印以 抑强秦,张仪入秦而复其衡,后破山东。曰:“昔在任人,帝曰难之,亦才矣。 〔注〕任,佞。才乎才,非吾徒之才也。”〔疏〕“仪、秦其才矣乎?迹不蹈已” 者,治平本作“迹”,而注文“仪不迹秦”作“迹”,今改一律。说文:“蹈,践 也。”论语云:“不践迹。”按:谓仪、秦之才,敻绝一时,后有作者,不能更践 其迹。“昔在任人,帝曰难之,亦才矣”者,音义:“任,音壬;难之,乃旦切。” 司马云:“宋、吴本作‘昔在任人,帝而难之,不以才矣'。难读如字。佞者,口 才也。舜谓知人安民,惟帝其难之;能哲而惠,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。杨子言驩兜 之徒能以巧言惑圣人,其才亦不在人下矣。”按:温公说是也。皋陶谟之“知人, 惟帝其难之”,即尧典之“难任人”,伪传训尧典之“难”为拒,而以皋陶谟之 “难”为如字。释文因于尧典“难”字音乃旦反,于皋陶谟无音,此妄生区别,非 古义也。此文“昔在任人,帝曰难之”,明以尧典之“难任人”与皋陶谟之“帝其 难之”为一事。难之为言,惮也。说文:“惮,忌难也。一曰难也。”盖不易谓之 难,知其不易而戒慎恐惧以临之,亦谓之难。问神云:“大圣之与大佞,难也。” 即任人难知之谓。此引书以明才之不尽可贵,谓佞人之为佞,虽聪明如尧犹难于别 之其才为何如。仪、秦之才,亦佞人而已,何足算哉!“才乎才,非吾徒之才也” 者,司马云:“口才,君子所不贵。”按:自“或问渊、骞之徒”至此,皆论先秦 之事。自“美行园公”云云以下,则论汉事也。注“仪不迹秦”。钱本“迹”作 “迹”,今依治平本。世德堂本无此语。按:弘范解此谓仪、秦不相蹈袭,秦言纵, 而仪言横也。吴云:“仪、秦虽同术,秦则务纵横,仪则务解之,二人之迹,各不 相蹈。”即李义之引伸,惟当云“秦则务纵”,衍“横”字耳。然二人不相蹈袭, 不必即为才。或人以为仪、秦之行事非后人所能企及,故谓之才。迹不蹈,即行事 不可企及之意。宋云:“言仪、秦之才术超卓自然,不践循旧人之迹。”亦非其义。 注“苏秦”至“山东”。按:治平本此注惟有“仪不迹秦”四字,以下全删。世德 堂本无此四字,而有“苏秦以下”云云。钱本并有之,今据补。“复其衡”钱本、 世德堂本作“复其卫”,乃形近而误。此用史记“成其衡道”语,作“卫”无义, 今订正。注“任,佞”。按:尔雅释诂文。世德堂本无此注。 |